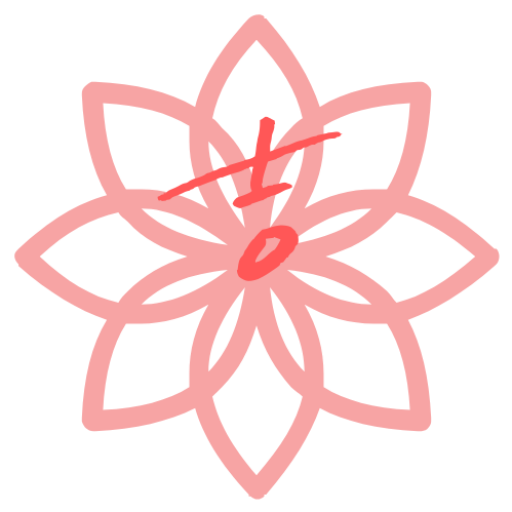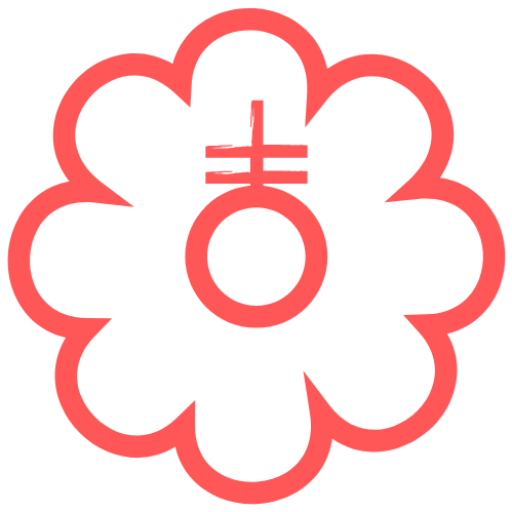漢娜.鄂蘭提出「平庸的邪惡」一說,來解釋納粹戰犯艾希曼的犯行,
即使沒有作惡的主觀意識,但因缺乏思想(thoughtless),而毫無意識的成為劊子手。
艾希曼並無「主觀為惡的意識」(有意的屠殺猶太人或作邪惡之事),
他也以「我沒有邪惡的意圖」為自己辯解。
但漢娜鄂蘭說,不是「無意為惡」就無罪,像這種情況是「平庸的邪惡」。
「平庸的邪惡」核心在於盲目或盲從,
服從不正當命令時說「我不知道」,或「我是為了保住工作或晉升」兩者並無差別
「不知道不對」是盲目,
「明知不對還服從」是盲從。
「不知道」或「服從」都不能作為理由,
而是自己放棄了自己道德思考或行動的「平庸」,助長了「邪惡」。
一味的「奉命行事」者因而成為邪惡的幫兇。
可知「平庸的邪惡」的定義有二:
1.緘默是罪
2.成為邪惡的幫兇/助長邪惡勢力
若身為軍警公教,如何避免自己成為「平庸的邪惡」者?
若我是六四天安門的坦克車駕駛、或者香港反送中的鎮暴警察,我該如何做?
我的回答是:
如果抗命的結果是我能承受的,我就接受。
如果懲處是我承擔不起的,我就設法操縱執法空間,盡量陽奉陰違,高高舉起、輕輕落下。
如果情勢逼迫我必須當場殺人,否則我會被就地處決,或許我會狠下心執行一次,但我也會立刻瞭解這工作我做不來,在最短時間內想辦法辭職(或逃或曠都行)。
如果時機或情勢允許,我會加入倒戈行列。
假設對抗邪惡的體制不惜犧牲生命是100分,一味奉命行事是60分。
即使做不到100分,但至少可以努力做到7、80分。
身為邪惡體制之下的執行者,知道有奉命行事之外不同的做法,
這個「有選擇」就是學習「平庸的邪惡」理論的意義與價值。
正如那個有名的「把槍口抬高一釐米」的故事(詳情請點這裡)–在柏林圍牆倒塌前,一位東德士兵開槍射殺一個試圖翻越圍牆到西德的青年。日後兩德統一,這名士兵被判有罪,法官說:「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,但打不準是無罪的。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,此時此刻,你有把槍口拾高一釐米的主權,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。」雖然這個故事與史實有所出入,但「把槍口抬高一釐米」的執法空間,確實是可以操之在己的。
某個出身警察的政治人物,早年擔任組長帶隊逮捕一位黨外異議人士,該名黨外人士拒捕自焚身亡。後來那位警察從政競選時,面對外界對此事的質疑,他回答:「當時我擔任最基層的刑事組長,奉各級長官命令辦事,接到高檢署簽發的限期拘票,若抗命就是瀆職,警察能抗命嗎?」、「若是時空背景再來一次,檢方再發一次拘票,我還是要去執行。」、「我做這件事情完全問心無愧、坦蕩蕩!」
我覺得他應當要道歉:「我很抱歉,當年我對民主自由的認知不夠,那位用生命來捍衛言論自由的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,我的做法不夠周全,造成了不幸的遺憾,這結果絕對不是我所願意見到的,若是時空背景再來一次,我會盡一切我所能做的努力來避免悲劇發生。」這是我替他擬的說詞,這樣說,總比說些什麼「我會再抓一次」之類的混帳話來得好,而且從他的回答,顯示他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錯、更不用說知道錯在哪裡,思維模式仍舊停留在威權時代。
即使他當年確實處於「不得不然」的位置,加上事發時解嚴未久,大多數人都「對民主自由的認知不夠」,軍警單位尤然,反倒那位自焚義士才是走在時代前端的先行者,因此我有一定程度能夠體諒他當年不懂得進步價值的侷限,不會太過苛責他的行為。問題是事隔多年之後,仍然沒有建立起「更高層次」的道德和正義觀念,毫無後悔愧怍的表示,甚至揚言「再抓一次」,依舊服膺「絕對服從」的威權體制,並把無限上綱的公權力等同自己「有魄力」,用來標榜自我形象,這就不值得原諒了。特別他還走上政治一途,執政者「政治不正確」更有可能帶來嚴重的災難,開時代倒車,把國家和人民都帶往回頭路,損害民主自由,還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麼問題。
其實,我在內的許多人希望看到的只是道歉而已,可是連這麼簡單的表示都做不出來,不禁使人浩嘆轉型正義的長路漫漫。希望現代公民能從歷史、哲學中學到更高層次的道德正義,一味知曉「奉公守法」只是硜硜然小人哉,能獨立價值判斷的智慧、有挺身而出的道德勇氣。才稱得上真正的大智大勇。